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二路6號1樓 Tel: (03)328-8833 E-mail: service@ncc.com.tw LINE: @nccs
本網站由 瀛睿律師事務所 擔任常年法律顧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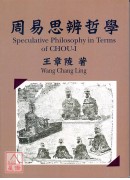




到底是儒家還是佛教,
能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
如果佛教可以取代儒家的地位,
成為抵抗西方文化入侵的主力,
那麼,
什麼形式或內容的佛教,才能勝任這一重擔?
對於中土,佛教原是異文化,交融後開出禪宗、淨土宗等屬己的花朵。此刻,面對歐美文化強力滲入的今日,佛教又該以何種面貌出現、以何種立場說話?本書是作者參與國內外佛教學術會議所發表的論文集,從證峰法師的「一佛」思想、太虛法師的「人生佛教」,延伸到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篇篇精闢,猶如檢視文化交鋒的斷層掃描。
序
古老的佛教,從釋迦牟尼的設宗立教迄今,雖然傳承延續兩千五百多年,然而在印度本土,卻只有一千七百年的壽命,便消失於印度歷史之舞臺。
以印度佛教而言,佛法崛起於印度文明之歷史舞臺,自有釋尊不共之創覺與特見。從原始佛教之簡樸平實,到部派佛教之紛諍分裂;而初期大乘之應運鼎革,批判傳統,開啟新機,都可以說是「思想」生命之再生。大乘佛教在印度本土,歷經法相唯識及真常如來藏,而後出現天神色彩濃厚的密教,終至佛梵不分,佛天一體而滅亡。印度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消失,固然有其內因外緣(回教入侵),如果只從內在因素考察,則佛教本身在「思想」方面,已由量變而產生質變,終至在思想上失去傳承力(契理),也失去創新的力量(契機),簡單的說:文化思想,如果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亦難逃緣起生滅的自然法則。
佛教傳入中國時,中國已有高度文化思想。印度民族性格的佛教,經過轉折融合成為中國民族性格的佛教。這點,從隋唐的天台及華嚴兩宗之出現,以及唐宋以來禪、淨兩宗的深入中國民間基層,可以反映出不同民族文化的「思想」交流下,新型態新文化展露的新風格。一千九百多年的中國佛教,固然有其光輝的史頁,而延續到明清,其思想演變幾乎已到「山窮水盡疑無路」了!清末民初以來,東西文化交流激盪,中國傳統文化(含儒、釋、道)在西潮沖激下,幾乎招架乏力!有心之士,莫不苦思探索,希望為全人類新文化新思想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
臺大哲學系教授,楊惠南居士新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便是站在以佛教立場為出發點,探索清末民初以來,從社會時空條件,以人物代表為線索,以「思想」探究評判為核心,試圖為「臺灣的佛教」思想界,開新徑尋出路。書中論題,牽涉廣泛,仁智互見,如何而找出定見,立方針。以思想界而言,層層出新,新環境新問題新人物,固難以定思想於一家也!此有漏世間,緣起法爾如是,不易增減也。
不過,楊老師的魄力及前瞻,其豪情壯志,真是使人由衷敬佩!其學養功力,亦令人十分讚嘆!經過楊老師對問題之探討,明白的指引我們思索的方向。我個人深信本書《當代佛教思想展望》,對研究佛教近代史的人,確能鼓舞我們,開拓佛教的新領域;對一位學佛的人,本書的啟示,回顧這些高僧居士大德的足跡,將深沉的影響我們,嚴肅的思索未來。
楊老師與筆者相識交遊,十有餘年,不嫌我的才疏德淺,徵序於鄙,辭不獲允,爰略舒管見感懷,權以為序也!
宏印法師 於海印精舍
自序
中國文化,遠則鴉片戰爭之後,面臨帝國主義及其夾帶進來之西方文化的無情衝擊;近則五四運動以來,受到主張「全盤西化」之人士的強烈批判。前者乃來自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之異族的強迫推銷,後者則是發諸自己同胞對於自己文化的盡失信心。然而,不管是來自異族的強迫推銷或發諸同胞的自我反思,對於一些優遊並信仰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士來說,無疑地,都是一場可怕的噩夢!
為了揮去這一噩夢,這些傳統中國文化的維護人士,提出了各種可能的因應之道。其中,主張義和團式地抵抗異族侵略者有之,主張「外須和夷,內須變法」或「維新變法」者有之,主張「中體西用」者有之。以清末、民初來說,在這些傳統中國文化的維護人士當中,受到西方文化最大衝擊和傷害的儒家人士,自然佔了絕大部分的人數;梁漱溟、熊十力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傳入中國已經千餘年,並和中國文化已經完全融合的佛教,在這場中、西文化的大衝擊中,由於遭受了魚池之殃,因此也和儒家一樣,出現許多有心的人士,毅然起來保護面臨存亡關頭的佛教。其中,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固然是三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但是歐陽漸(竟無)和太虛大師,以及太虛大師的學生——印順導師,卻也是其中不可或忘的人物。
值得玩味的是,上面所提到的這些佛、儒二家中的人士,儘管在思想上、師承上,甚或學派上,有著不盡相同的背景,但是,彼此之間卻大都相互往來,以致存在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就以代表儒家文化的梁漱溟和熊十力來說,他們都出自歐陽漸所創辦的「支那內學院」,跟隨歐陽淅學習唯識學。熊十力之所以能到北京大學教書,還是歐陽和梁漱溟合力向蔡元培校長推薦的結果呢!而太虛大師則創辦了「閩南佛學院」,印順導師即是該院的學生兼老師。而且,支那內學院和閩南佛學院的師生之間,也常有書信、文章的往來討論和批評。例如,太虛大師和歐陽漸、梁漱溟、熊十力之間,就曾有書信的往來和文章上的交會。屬於兩院學生輩的熊十力和印順導師之間,也曾環繞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一書,展開極具火藥味的辯論。甚至同屬支那內學院的歐陽漸,梁漱溟和熊十力之間,也曾因為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一書,而有一些文字上的往返辯論;而印順導師,也曾站在「人間佛教」的立場,對其老師——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展開評論。這些林林總總的討論和批判,豐富了民國初年的中國佛學界和一般的思想界。而他們所一再關心的問題有二:(1)到底是儒家或是佛教,才能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2)如果佛教可以取代儒家的地位,成為抵抗西方文化入侵的主力,那麼,什麼形式或內容的佛教,才能勝任這一重擔?
對於第(1)個問題,代表儒家的梁漱溟和熊十力,以及代表佛教的歐陽漸、太虛大師和印順導師,他們之間必然不會有共同的結論;因此成了各說各話,但卻不失精彩的主張和對話。至於第(2)個問題,支那內學院的歐陽漸認為:(由中國玄奘、窺基所弘傳的)印度無著、世親的唯識學,才是唯一能夠勝任的佛法。然而太虛大師則以為:發展自中國本土的佛教宗派,例如禪宗和天台宗等——他所謂的「法界圓覺宗」,才足以勝任抵抗西方文化的重擔。但是,太虛大師的這一主張,有一先決的條件:中國本土所發展出來的宗派——「法界圓覺宗」,必須在寺廟的制度、財產上有所改進,並且更加強調佛法的「人生」性,亦即更加重視還活著的「生人」,否則即無法肩負這一重責大任。就寺廟制度、財產的改進而言,即是太虛大師有名的「僧制、寺產革命」;而他所強調的重視「人生」或「生人」的佛教,即是他那有名的「人生佛教」,那是他的「教理革命」中的主要部分。「僧制」、「寺產」和「教理」三種「革命」,構成了太虛大師有名的「佛教革命」的全部。
而太虛大師的學生——印順導師,則有不太一樣的看法。他並不是一個十分關心「中國文化」的人,也不是一個在意西方文化是否入侵中國的人。他所關心的毋寧是:「純正」的佛法,是否能夠更加廣泛而又無誤地在中國甚至全世界流傳的問題。基於這樣的理念,印順導師展開了對他的老師——太虛大師所心儀的「法界圓覺宗」的批判;相反地,他呼籲:回歸純正的印度佛法,亦即回歸原始佛法和初期大乘佛法——中觀學派!他認為,這樣的佛法,才能對治傳統中國佛教的弊病——渡亡、渡鬼、偏重死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偏重天神信仰等弊病,使得中國佛教,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之下,起死回生。他認為,太虛大師所提倡的「法界圓覺宗」和三種「佛教革命」,最多只能解決中國佛教注重渡亡、渡鬼、偏重死後往生的弊病,但卻無法消除中國佛教偏重天神信仰的特色。只有他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才能一方面解決中國佛教偏重渡亡、渡鬼、死後往生的弊病,二方面又消除中國佛教偏重天神信仰的特色。如此一來,中國佛教才能不偏於鬼道和天道,而成為重視人道的「人間佛教」。
筆者很驚訝地發現:不管是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或是閩南佛學院的印順導師,都看出中國佛法的積弊難改,而試圖帶領整個中國佛教,回歸到印度佛法上去。在這一意義之下,太虛大師對於中國佛教的批判,只能算是為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打前鋒,做一鋪路的工作罷了!
本書所收錄的幾篇論文,主要的即是集中在以上所說之中國佛教現況的討論。這些論文,都曾口頭宣讀於國內、外的學術會議之上。其中有兩篇——〈臺灣佛教的「出世」性格與派系紛爭〉和〈臺灣革命僧——證峰法師(林秋梧)的「一佛」思想略探〉,則是有關臺灣佛教現況的報告和討論。在這兩篇有關臺灣佛教的文章當中,由第一篇可以看出臺灣佛教受到中國佛教深重的惡質影響;特別是在一九四九年政府退守臺灣之後,這一情形尤其顯著。而從第二篇論文,可以看出:一九四九年前,臺灣原本也有自己的佛教。這一具有臺灣本土特色的佛教,即是普遍和農工階級互相結合以反抗統治階級的佛教。無疑地,它是因為臺灣長期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高壓統治之下,所孕育出來的反抗佛教;它可比美於當代西方基督宗教所發展出來的「激進神學」(Radical Theology)和「解放神學」(Theology of Liberation)!
筆者身為臺灣佛教信仰中的一員,僅以這兩篇文章,來和讀者見面,無疑地,應該感到不安和慚愧!這兩篇文章最多只能扮演拋磚引玉的角色,希望會有更多的學者,來共同投入臺灣佛教的研究之中!在當前許多人雖然身住臺灣,卻又不敢「大聲喊出愛臺灣」的政治現況之下,做為一個頂天立地而又熱愛臺灣的臺灣人,也許,臺灣佛教的研究,將是筆者今後所應致力的方向吧!
最後,筆者應該向讀者道歉的是,本書雖然是「當代」中國和臺灣佛教的研究成果報告,但是,其實並不是全面性地討論到當代中國和臺灣佛教的各個層面。例如,雖然出身內學院的熊十力,本書在〈儒家在印順導師之「人間佛教」中的地位〉一文當中,曾有討論;但是更重要的人物,毋寧是他的老師——歐陽淅的唯識學,在本書當中,竟然沒有隻字片語的說明!又如所謂的「民國四大師」當中,本書只討論了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對於另外的三位大師——虛雲大師、印光大師和弘一大師(李叔同),也完全沒有交代!無疑地,這是種缺憾!
本書沒有涉及歐陽漸的研究,誠然是最大的遺憾!這個遺憾,也許可以在下面稍做補救;而更加深入、詳盡的研究,只有留待以後了!不過,本書沒有把虛雲大師、印光大師和弘一大師列入研究範圍之內,卻有充足的理由。這一理由是:筆者所長期關心的是佛教的「現代化」問題,因此和這一主題不相干的人物,往往就被筆者所忽略。而不管是虛雲大師、印光大師或是弘一大師,幾乎都是不關心世事的人。即使像印光大師那樣,曾表現出痛心八年抗戰冤死的亡魂,但也僅止於傳統的表現方式——舉辦念佛法會,祈求「國泰民安」!無疑地,他們都是試圖回到曾經燦爛一時的傳統中國文化(佛教)的美夢中去;至於佛教如何「現代化」?對他們來說,那是從來就不曾意識到的問題!(筆者曾寫有一篇有關虛雲大師禪法的論文,口頭發表於臺灣佛教界為紀念虛雲大師一百五十歲冥誕的學術研討會上,但因該文與本書主旨不合,只有另書出版了。)
最後,我們可以來談談歐陽漸居士的唯識學了。首先,他認為只有佛法才能拯救中國,甚至拯救世界。他說:「方今時勢之急,既有若此,然而求識近代學說能有挽此狂瀾預防大禍者,縱眼四顧,除佛法曾無有二……。」(引見〈佛法為今時所必需〉)他認為,不管是科學或是(西方的)哲學,都已發展到偏頗的地步,因此絕對無法拯救中國和世界。例如,就(西方的)哲學來說,他曾在〈佛法為今時所必需〉一文當中,做了這樣的分析和批評:
是故今日哲學界之大勢,一方面為羅氏之現象論,一方面為柏氏之直覺論,由前之勢必走入懷疑,由後之道必走入獨斷。……抑又以理推之,今後之哲學當何如耶?吾意繼羅柏而起者,必有風行一世之虛無破壞斷滅派……以羅氏之理論,加入柏氏之方法,自茲而後,由懷疑而武斷,由武斷復懷疑,於外物則一切皆非,於自我則一切皆是;又復加以科學發達以來,工業進步,一面殺人之具既精,一面貧富之差日遠,由茲怨毒潛伏,苦多樂少,抑鬱憤慨之氣,充塞人心,社會人群既無可聊生,從而主張破壞,主張斷滅,機勢既順,奔壑朝東,是故吾謂二氏之後,必有風行一時之虛無破壞斷滅派出世也。
引文中所提到的「羅氏」是英國哲學家羅素(B. Russell, 1872-1970),而「柏氏」則是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 Bergson, 1859-1941)。歐陽居士認為,前者的哲學將導致「懷疑論」,後者的哲學則將導致「獨斷論」。這樣一來,懷疑論和獨斷論互相激盪,再加上科學工業所帶來的副作用,最後必然導致「虛無破壞斷滅派」的產生。那時將是人類的浩劫!所以,歐陽居士痛心疾首地呼喚著:「諸君!諸君!此時非遠,現已預見其倪,邪思而橫議,橫議而狂行,破壞家庭,破壞國家,破壞社會,破壞世界,獸性橫流,天性將絕!」(引見〈佛法為今時所必需〉)因此,歐陽居士認為:只有佛法才能拯救這一日漸沉淪的現象!
然而,歐陽居士所認為的,能夠拯救中國和世界的「佛法」,到底是什麼樣的佛法呢?無疑地,那是他所弘揚的唯識法相學(詳下文)。另一方面,他卻極力反對中國傳統佛教所發展出來的禪宗、淨土、天台、華嚴等教派。他對於禪師們「徒拾禪家一二公案為口頭禪,作野狐參,漫謂佛性不在文字之中」,而對「前聖典籍,先德至言,廢而不用」的作為,強力表現出他的不滿。他對淨土宗徒「執一行一門以為究竟」的態度,不表同情。他對天台、華嚴二宗,有更露骨的批判:「自天台、賢首等宗興盛而後,佛法之光愈晦。」禪、淨、天台和賢首等三者,是他對於中國佛教所舉出的「五蔽」當中的三蔽。而他的結論則是:「欲祛上五蔽,非先入唯識法相之門不可!」(以上皆見歐陽漸〈唯識抉擇談〉)
歐陽居士為什麼認為「唯識法相學」,能夠對治中國佛教的「蔽(病)」呢?原因是:唯識法相學「非宗教非哲學」,當然也不是科學。它能夠對治「宗教之神秘」、「宗教之迷信感情」。而且,由於唯識法相學的「精深有據」、「超活如量」,可以補救宗教、科學和哲學的偏失。這些觀點,可以從他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學〉等文當中看出來。例如,在〈與章行嚴書〉一文中,他即曾經這樣說:
佛法之晦,一晦於望風下拜之佛徒,有精理而不研,妄自蹈於一般迷信之臼。二晦於迷信科哲之學者,有精理而不研,妄自屏之門牆之外。若能研法相學,則無所謂宗教之神秘;若能研唯識學,則無所謂宗教之迷信感情。其精深有據,足以破儱侗支離,其超活如量,足以藥方隅固執,用科哲學之因果理智以為治,而所趣不同,是故佛法於宗教科哲學外別為一學也。
其次,歐陽居士所說的「唯識法相」,是指印度「護法系」的唯識學;亦即玄奘大師及其弟子窺基所弘揚的唯識學。所以他說:「剋實而談,經論譯文,雖有新舊,要以唐人(指玄奘大師)新譯為勝。」又說:「又談著述,唐人(指玄奘、窺基等大師)亦稱最精。」(皆見〈唯識抉擇談〉)至於,他區分「唯識」和「法相」二學的不同,也是古來少見,以致成為當時一些唯識學者所爭議的焦點;無疑地,這也是他的唯識學的特殊之處。但是由於篇幅所限,只有另文討論了。(一個簡略的說明,請參見歐陽居士的一篇短文:〈與章行嚴書〉。)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歐陽居士是當代「居士佛教」的大力推動者。他是一個十分看不起出家僧人的居士,他在〈辨方便與僧制〉文中,曾說:「中國內地僧尼約略總在百萬之數,其能知大法、辨悲智、堪住持、稱比丘不愧者,誠寡若晨星:其大多數皆遊手好閒、晨夕坐食,誠國家一大蠹蟲!但有無窮之害,而無一毫之利者!」因此,相對地,他提倡以在家人為主的「居士佛教」。他在〈支那內學院院訓釋.闢謬(5)〉中,曾列舉了「十謬」,其中有幾條牽涉到出家僧人和在家居士之間關係的內容;例如,「居士非僧類,謬也」、「居士全俗,謬也」、「居士非福田,謬也」、「在家無師範,謬也」、「白衣不當說法,謬也」、「比丘不可就居士學,謬也」、「比丘絕對不禮拜(居士),謬也」、「比丘不可與居士敘次,謬也」!
歐陽居士所在的時代,是佛教沒落到「谷底」的時代,出家僧人的素質、地位,到了極須改革的地步。因此,他所試圖建立起來的「居士佛教」,可以說是當時佛教現況的自然反應。然而,這一問題,即使到目前,都是甚具爭議性的問題。事實上,太虛大師站在出家僧人的立場,即曾表示頗不以為然的態度。儘管是這樣,歐陽居士所建立起來的「居士佛教」之典範,仍然可以提供未來居士佛教建立「(居士)僧團」的良好參考。
最後,筆者還願提出說明的一點是:熊十力的「體用合一」論,多少可能受到他的老師——歐陽居士之「體用合一」論的影響。歐陽居士在〈唯識抉擇談〉中,曾以「體中之體」(一真法界)、「體中之用」(二空所顯真如)、「用中之體」(種子)、「用中之用」(現行)等四句,來說明「體」與「用」之間的關係。然後又說:「生滅向流轉邊是為有漏,向還減邊是為無漏。從來誤解生滅之義,以為非無漏果位所有,所據以證成者,則《涅槃》『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之文也。此蓋不知寂滅為樂之言非謂幻有可無,大用可絕。滅盡生滅別得寂滅,亦幾乎斷滅之見而視佛法如死法也……。」又說:「有為不可歇,生滅不可滅」。又說:「凡法皆即用以顯體」。由這些片斷,可以看出歐陽居士並不認為涅槃(寂滅)之後,即是虛無而沒有「幻有」、「大用」存在的狀態。相反地,那是「有為不可歇,生滅不可滅」的狀態。因此,《涅槃經》中所謂「寂滅為樂」的意思應該是:世俗的生滅現象被消滅而達到「寂滅」的狀態時,即是大用流行的妙樂產生之時!無疑地,這和熊十力所了解的「體用合一」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那麼,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到底「新」在哪裏呢?
本書的出版,只有一個目的:透過當代中國和臺灣佛教思想、現況的討論,為未來的佛教尋找出一條健康而又可行的發展道路!讀者從〈臺灣佛教的「出世」性格與派系紛爭〉一文當中,可以看出當代臺灣佛教以及中國佛教,已經發生嚴重的缺失,因而已經走到必須改弦易轍的關鍵時刻。佛教是一個「活著的」宗教,而不是死去了的、歷史上的宗教,不能只是當做學者研究的對象。關心它的學者,必須「進入」它的裏面,和它合一,成為自己生命的全部。不能把它看成外在於自己,而和自己不相干的「研究對象」。關心佛教的學者,一定會同意:佛教不是外在於研究者的「客體」,相反地,它必須成為研究者的「主體」!在這樣的體認之下,每一個關心佛教的學者,必然會追問:既然佛教是「活著的」宗教,它必須像是一株生氣蓬勃的巨樹,繼續地茁壯下去!那麼,佛教何去何從呢?是走回衰退的、傳統的老路、死路呢?或是另闢蹊徑,開拓更加廣大的發展空間呢?這是每一個關心佛教未來的人士,所必須面對的問題。本書的幾篇文章,提供了當代佛教的現況說明,希望經由這一說明,能夠引起更多關心當代佛教的人士,來參與討論和研究。這是拋磚引玉的工作,因此,本書取名為《當代佛教思想展望》。
最後,還要特別感謝宏印法師,在百忙中為本書寫序!
楊惠南
寫於臺灣大學哲學系
四月八日佛誕節
目錄
序/宏印法師
自序
臺灣佛教的「出世」性格與派系紛爭
臺灣革命僧——證峰法師(林秋梧)的「一佛」思想略探
從「人生佛教」到「人間佛教」
太虛之「人生佛教」和梁漱溟之「人生三路向」的比較
佛在人間——印順導師之「人間佛教」的分析
儒家在印順導師之「人間佛教」中的地位